《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
 (资料图)
(资料图)
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胡适,其对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源流和作者的考证,曾被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誉为是“国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中当然包括胡适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的精彩考证。
胡适坚信《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读者或许了解《醒世姻缘传》的故事梗概:主人公狄希陈的前生为晁源,他曾狩猎时射死一只狐狸,还把狐皮剥了;因为宠爱他的小妾珍哥,将他的妻子计氏逼得自杀。晁源托生为狄希陈,狐狸托生为他的妻子薛素姐,计氏托生为他的小妾童寄姐,狄希陈特别怕老婆,而且受到妻妾的各种虐待,后来幸得高僧指出前世因果,虔诵佛经,才消除冤业。作者“西周生”由此引出一条所谓的“通则”: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
这部小说的著者真的是蒲松龄吗?由于胡适在这篇考证文章中特别突出思想方法的意义,强调通过这篇文章“要把金针度与人”,我们就不妨一起仔细检视胡适的考证方法和证据。
首先,胡适大胆假设《醒世姻缘传》的著者“西周生”就是蒲松龄,因为他发现这部小说的两世的恶姻缘叙事结构和《聊斋志异》中《江城》篇非常类似。
《醒世姻缘传》接下来就是小心求证,这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内证。所谓内证,就是对两部小说文本进行细致比较,从而寻找相应证据。第一,胡适认为这两部著作都非常注意夫妇的问题,都特别用力描写“悍妇”的凶恶。
第二,《聊斋志异》中有多篇文章都表现出蒲松龄尤其用力描写夫妇之间的苦痛,无论是实写的工笔细描还是虚写的写意传神,两部著作在写作手法方面皆非常相似。
但是,内证的说服力仍然有限,因为这既有可能是巧合,也有可能是后人对《聊斋志异》的模仿,并不能证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就是蒲松龄。
胡适显然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到处搜集外部证据,这就涉及外证。
第一,乾隆辛卯(1771)年进士杨复吉(1747—1820)在《梦阑琐笔》中提到代赵起杲(1715—1766)刊刻《聊斋志异》的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鲍廷博(1728—1814)说起蒲松龄是《醒世姻缘传》的作者。
第二,孙楷第(1898—1986)用《醒世姻缘传》所记的地理、灾祥、人物三项和济南府属各县地志进行参互比较,推测该书的地理是章邱、淄川两县,著书年代应在崇祯、康熙间,著者可能是蒲松龄。
第三,将《醒世姻缘传》和蒲松龄的《聊斋白话韵文》中土语土词进行对比,二者存在诸多相似或一致的地方。
第四,《醒世姻缘传》和《聊斋志异》对“悍妇”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社会因为离婚困难,男人在婚姻中同样可能遭受痛苦的基本事实。(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中国旧小说考证》,李小龙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00—262页。)
胡适的考证虽然精彩,但是仔细检视胡适的考证方法和证据不免令人产生诸多疑问,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第一,如何识别蒲松龄的独特文学风格?第二,《聊斋志异》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特定社会现实的回应?
评点《聊斋志异》的三种视角
相信读者阅读蔡九迪(Judith Zeitlin)关于《聊斋志异》研究的经典著作后就会对上述两个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蔡九迪现为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这部著作是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仔细修订后于199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即获得美国学术界的关注。
江苏人民出版社于今年推出的中译本《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该书主要通过对《聊斋志异》文本的精细阅读和中西文化比较,以此阐明《聊斋志异》文学叙事的意蕴并展示明清文人丰富的精神世界,该著既是一部文学研究著作,也是一部明清文化史研究著作。该书首先直面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部充满各种奇幻故事的志怪小说,如何理解《聊斋志异》中的“异”?在蔡九迪看来,物之“异”并不在物自身,而在于观看者或者阐释者的主观理解,如何理解“异”和阐释者所处的文化环境紧密相关,“异”与“常”之间的边界从来都不是固定的,相反却是不断更新、模糊或重新定义的,如果“异”是可以界定的,那也必须在历史和小说、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变动中加以界认。所以,蔡九迪既非将文本世界和生活世界对应,也非将二者隔绝,而是认为二者在不断游移,借用《红楼梦》中的一副对联,正所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因此,她首先梳理了17—19世纪《聊斋志异》的阐释史,以此为读者阐释不同时代的读者是如何理解和阐释“异”的,这也正如德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汉斯·姚斯(Hans Jauss, 1921—1997)在其名作《文学史作为对文艺理论的挑战》中所说的,一部文学作品并非对所有读者都呈现相同图景,这是蔡九迪该著中颇具启发性的部分。她将关于《聊斋志异》的评点话语概括为三种视角:第一种是将记叙“异”的做法合法化;第二种是将其视为严肃的自我表达寓言;第三种是将它视为文风优美的伟大小说。
第一种视角主要是强调“异”和道德秩序的一致性而将“异”合法化。这方面代表主要是高珩(1612—1697)和唐梦赉(1628—1698),这两位名士在当时淄川地区具有显赫的社会和文学声望,而且作为蒲松龄的私交,曾为蒲松龄提供创作素材。他们通过援引儒家经典而将“异”重新定义,从而将“异”重构为在儒家道德和思想上可被接纳的概念,把边缘化的志怪文学传统纳入志主流文学和哲学范围内,志怪故事的道德性最终依赖于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文学虚构是“异”,教化人心是“正”,二者并非水火不容。这类传统努力在主流文学和思想传统中为志怪文学开辟出容身之一隅,并赋予其纯正的出身和道德认同。
第二种视角则是将《聊斋志异》与志怪文学相分离,从而把该著视为蒲松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表达。蒲松龄长期科场失意,满腹才华却抑郁不得志,成为清代那些心系天下却屡遭挫折的失意文人的缩影,张元(1672—1755)在《柳泉蒲先生墓表》曾评论道:“先生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然入棘闱辄见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决然舍去,而一肆力于古文,奋发砥淬,与日俱新。”(张元:《柳泉先生墓表》,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附录一,胡适:《中国旧小说考证》,李小龙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54页。)在《聊斋志异》中,那些妖魔鬼怪成为人类邪恶性的透明符号,而官僚化的阴曹地府是对腐败官场的讽刺。当然,这种表达并非意味着《聊斋志异》完全是对社会现实的讽刺,清代著名藏书家孔继涵(1739—1784)预设《聊斋志异》的三类读者:浅薄的读者只是沉浸于“异”的魅惑;教条主义者则满眼只是该著隐含的道德和讽刺含义;高明的读者则看到该著的表层和深层意义,“异”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现象,是表面魅惑与内在道德诉求的相互平衡。这类传统将这部作品归为自我表现的寓言式作品,具有同类作品通常不具有的文学价值,努力提升这部志怪故事集的品位。
第三种视角则不再将“异”视为备受争议的问题,认为这部著作的价值既不在于其所蕴含的对宇宙大道的洞悉,也不在于其隐含的寓言式自我表达,而是其文学风格与叙事技巧。清代学者冯镇峦(1760—1830)将《聊斋志异》和《水浒传》及《西厢记》相提并论,认为这三者都是“体大精思、文奇义正”,他将《聊斋志异》视为一部创造性的小说,他更关注的是该著本身的文学风格,而不再是这部小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他严厉批评那些仿作:“无《聊斋》本领,而但说鬼说狐,侈陈怪异,笔墨既无可观,命意不解所谓。”由于对虚构性想象的不屑在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他对此进行反驳:虚构本身并非问题,关键在于作者是否具有足够的技巧让读者信服。第三类传统超越对《聊斋志异》一书志怪内容的关注,而是将评论者自身的文名和这部经典小说联系在一起,他们更多关注《聊斋志异》本身的文学风格。
那么,蔡九迪选择何种视角评论《聊斋志异》?可以看到,蔡九迪的研究重要启发在于,她既受到这三种视角的影响,但又明显不同:她以文化史的视野将文本世界和生活世界进行整合,从而把对《聊斋志异》文学叙事的分析置于明清文人丰富的文化世界语境中来进行,以此展示蒲松龄独特的文学风格与明清士人文化的复杂关系。
《聊斋志异》与明清文人的精神世界
蔡九迪对《聊斋志异》的评论不再着眼于志怪故事等早已成为这部小说的标签内容,而是深受文化理论的影响,转而将目光转至对16—17世纪中国士人文化颇为关注的三个重要主题即“癖好”“性别错位”“梦境”的分析上,以此展示蒲松龄如何更新“异”这一文学范畴。在蔡九迪看来,这三大主题均涉及对人生经验中基本界限的跨越:“癖好”跨越了主客关系;“性别错位”则跨越了男女界限;“梦境”则跨越了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因此,蔡九迪在这部分内容中绕开通常关注的志怪文学的标签,而是将重点放在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如何通过不断操控界限来实现相应创作目的,这也是该著的重要特色。
首先,蔡九迪对蒲松龄的文学叙事的分析和明清士人的“癖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蔡九迪看来,尽管对“癖”的理解不同,但还是存在若干基本原则:“癖”是对特定事物或活动的习惯性依恋;这种依恋同时是过度且执着的行为;“癖”同时指一种蓄意反传统的怪异姿态。对“癖好”行为的识别和人们对这一行为的态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则呈现不同状态:魏晋时期则带有超然隐逸和不受传统拘束的意味;晚唐和两宋时期则开始和鉴赏相关;到晚明则成为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爱好者则会竭力声称他们会忠于他们所爱之物的这些品质。以《聊斋志异》中的《石清虚》为例,蔡九迪详细评点了蒲松龄的文学叙事和晚明的“癖”文化的关系,《石清虚》主要讲述了狂热的石头收藏者和一块名为“石清虚”的石头之间的友情,最终以彼此的自我牺牲而达到顶点。在她看来,蒲松龄选择“石癖”并非偶然,他笔下爱石之人的创作灵感显然来自宋朝书法家米芾(1051—1107)的佚事,同时蒲松龄以小说家技巧将无生命的物和人之间的强烈的爱,以一种连贯的叙述结构呈现,进一步发展明末著名学者李贽(1527—1602)相应思想。
与此类似,蔡九迪详细阐释了《聊斋志异》中跨越男女性别的叙事所隐含的文化意蕴。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她关于《聊斋志异》中“悍妇”形象的分析,蔡九迪并不认可胡适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的考证,因为“悍妇”这一主题在17世纪广泛存在,正如蒲松龄在《江城》中曾评论道:“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悍妇本身的形象在文学中习以为常,根本不足以作为证据。在蔡九迪看来,蒲松龄对关于“悍妇”程式化的情节的突破倒是创造了“良性悍妇”这一形象,她们虽然性格与大多数“悍妇”相同,比如破口大骂、残忍凶暴,但是给家庭带来的却是福祉而非灾难,比如在《云萝公主》中,云萝公主的小儿子可弃道德败坏,可弃的妻子是一个可怕的悍妇,手拿菜刀将可弃赶出家门,最后可弃改邪归正,家道日兴,蒲松龄对此揶揄道:“悍妻妒妇,遭之者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 ,非参、苓所能及矣。”所以对付这类人,就只能使用这种“以毒攻毒”的办法了。
或许令多数读者最感兴趣的是蔡九迪对《聊斋志异》中关于梦的叙事与明清文人关于梦境迷恋的复杂关系的细致分析,这其实也是最能体现“亦幻亦真”的部分。《聊斋志异》中共有八十余篇与梦境有关的故事,此外还有二十五篇是直接以梦为主题的,蒲松龄既延续了中国梦境文学的传统,也保留了明清士人关于梦文化的迷恋。在蔡九迪看来,《聊斋志异》对梦境的偏好反映了当时文人圈热衷于梦境的文化现象,明清文人对梦境的广泛兴趣不仅体现在戏曲和小说中,同时还体现在专论、汇编、散论,以及自传、诗歌,甚至绘画和版画中,而这或许与明代遗民通过谈梦而表达对前朝的追忆有关。蒲松龄受明清士人对梦文化的迷恋的影响,比如他最青睐的一种手法就是将过度使用的比喻格加以反转,恢复其原有的新奇感,这是其处理与人生如梦有关的主题时常用的一种手段,尽管在《聊斋志异》中梦并不具有特定的遗民象征,但是在此类故事中仍然常带有一种忧郁的感伤,这种对梦境的挽歌更像是对一个已经消逝了的过往的追忆的隐喻。
总之,蔡九迪的这部著作重要启发之处在于,她没有将一部文学作品和现实世界简单对应,也没有将二者完全隔绝,而是从文化史视角将对蒲松龄的文学叙事风格的分析放置于明清士人精神世界的语境中进行,以此来展示蒲松龄是如何更新“异”这一独特的文学范畴,这是以往研究者所较少关注的。
由此亦可以看到,蔡九迪和胡适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代表了两种进路:前者并不在意文本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而是更注重阐释文本和叙事的文化意蕴;后者更注重文本和现实世界的紧密关系,努力发现与文本相关的基本事实。两种研究进路并无高下之别,相反却是彼此有益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蔡九迪将蒲松龄如何持续更新“异”这一范畴的分析放置于明清士人文化的语境中,但是二者本身即具有一定张力,因为文化本身具有相对普遍性,而志怪文学的特性恰在于其故事内容独特。
因此,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品之作,《聊斋志异》几百年来能够吸引诸多读者,显然不在于它的道德说教,也不在于它对社会生活有多大程度的反映,甚至不完全在于蒲松龄的那些文学技巧,更为基础的是它的实质内容即故事本身的新颖性,实际上蔡九迪最后的评论也点明了这点:当我们读了其他故事,本以为画像要变幻为人时,人却进入了画中;读了公案小说,当我们期待案件大白于天下,凶犯被正法时,男扮女装的采花贼却被阉割而得以善终,正是这种持久地激起读者的惊愕并挫败其期待,才是《聊斋志异》的重要魅力。其实,这也正是这部古典小说自近代以来就不断被诸多海外学者翻译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深刻证明,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一定能够跨越中西文化界限。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我读︱《异史氏》古典小说的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胡...
-

李玟丈夫声明:我和CoCo婚后一直保持财产独立,未来也不会参与CoCo有关财产分配的任何事宜
李玟丈夫声明 我和CoCo婚后一直保持财产独立,未来也不会参与CoCo有关
-

加快扩建!湖北这座机场有新消息!
加快扩建!湖北这座机场有新消息!
-

生态环境部:对造假行为决不放过
本报北京7月27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张艺)有的拔掉或者遮挡采样探...
-

7月27日基金净值:易方达中证红利ETF最新净值1.3351,涨0.1%
7月27日,易方达中证红利ETF最新单位净值为1 3351元,累计净值为1 4811
-

创造101抱王一博的女生(创造101王一博抱徐梦洁是哪一期)
《创造101》第3期选手徐梦洁在节目中一个环节,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然
-

7月27日基金净值:华泰柏瑞富利混合A最新净值2.0415,跌0.46%
7月27日,华泰柏瑞富利混合A最新单位净值为2 0415元,累计净值为2 0415
-

东京7月CPI同比上涨3.2%
【东京7月CPI同比上涨3 2%】日本总务省7月28日发布数据,东京7月整体消
-

宝沙发展(01069):所有复牌指引已获达成 7月28日复牌
智通财经APP讯,宝沙发展(01069)发布公告,董事会认为所有复牌指引已获
-

生态环境部:推动出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
7月27日,据中国网,国新办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
-

新民快评丨让孩子远离“毒视频”
儿子14岁,功课多了起来。他和我一样,喜欢用刷短视频来缓解压力。我喜
-

体育贵州 活力贵定 2023年贵州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落幕
7月27日,“体育贵州活力贵定”2023年贵州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在贵定...
-

美国7月堪萨斯联储制造业综合指数为-11
美国7月堪萨斯联储制造业综合指数为-11,预期-10,前值-12。(文章来源
-

美容美发学几年(如果去读美容美发学校的话一般多长时间能毕业)
1、一般的话要几个月,最好建议你至少读到中级班(要两个月),如果读高级
-

2023中级会计职称考试准考证打印入口网址
2023年中级会计职称考试准考证打印时间(省份索引)北 京天 津河 北
-

小鹏官宣大众7亿美元入股4.99% 将联合开发两款B级电动车
战略技术合作的目标是利用双方的互补优势,建立长期双赢的战略合作关系
-

梦幻西游阵法相克一览表(梦幻西游阵法相克.)
1、梦幻西游中的阵形一共有9种,相信大家早就已经知道了——普通阵...
-

南昌天香园门票老人可免费吗?
南昌天香园门票老人可免费吗?65周岁(含)以上凭老年人或身份证[免费];60
-

孩子被蚊虫叮咬后,怎么用药好得快?
孩子被蚊虫叮咬后,怎么用药好得快?,过敏,瘙痒,细菌,小包,蚊子,害虫,
-

公司是否有城中村改造项目?合肥城建回应
每经AI快讯,有投资者在投资者互动平台提问:董秘您好,请问公司是否有
-

2023年浪卡子县退休人员工资补发标准 附西藏养老金调整细则公布
养老金主要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过渡性调节金
-

鹰城交警走进平顶山日报社,送上“交通安全课”
“只喝一口啤酒就能吹出醉驾!”“以后一定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喝酒...
-

我国成为世界少数几个掌握第四代核能技术的国家之一
央视网消息: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电站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座
-

金庸是参照贾宝玉写张无忌?看这处情节,还真是这么回事!
《红楼梦》中,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也是这样,把下人身份的平儿认作主子
-

尼日尔突发政变,中方表态
当地时间26日凌晨,尼日尔总统卫队部分军人扣押总统巴祖姆。在27日的中
-

科尔:安东尼好几次惯用脚射门都没打正这可不行,他得多进球
安迪-科尔在接受MUTV采访时表示安东尼要提升自己的射术,取得更多进球
-

株洲“打非治违”第五批典型案例曝光
超标存储药剂,没有焊工证就上岗作业,安全监管松散……近日,株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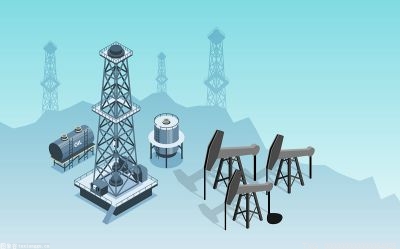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丨南召县:创新高地产业兴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廖涛距离二广高速南召站一公里处,就是“中...
-

大宗交易:工商银行成交180.52万元,折价11.28%(07-27)
2023年7月27日,工商银行发生1笔大宗交易,总成交43 29万股,成交金额1
-

境外电诈犯罪集团大肆组织、拉拢、欺骗、利诱一些年轻人参与犯罪——政法机关持续加大打击惩处力度
在高回报诱惑下,有人偷渡奔向幻想中的“海外淘金地”,期待“一夜...



